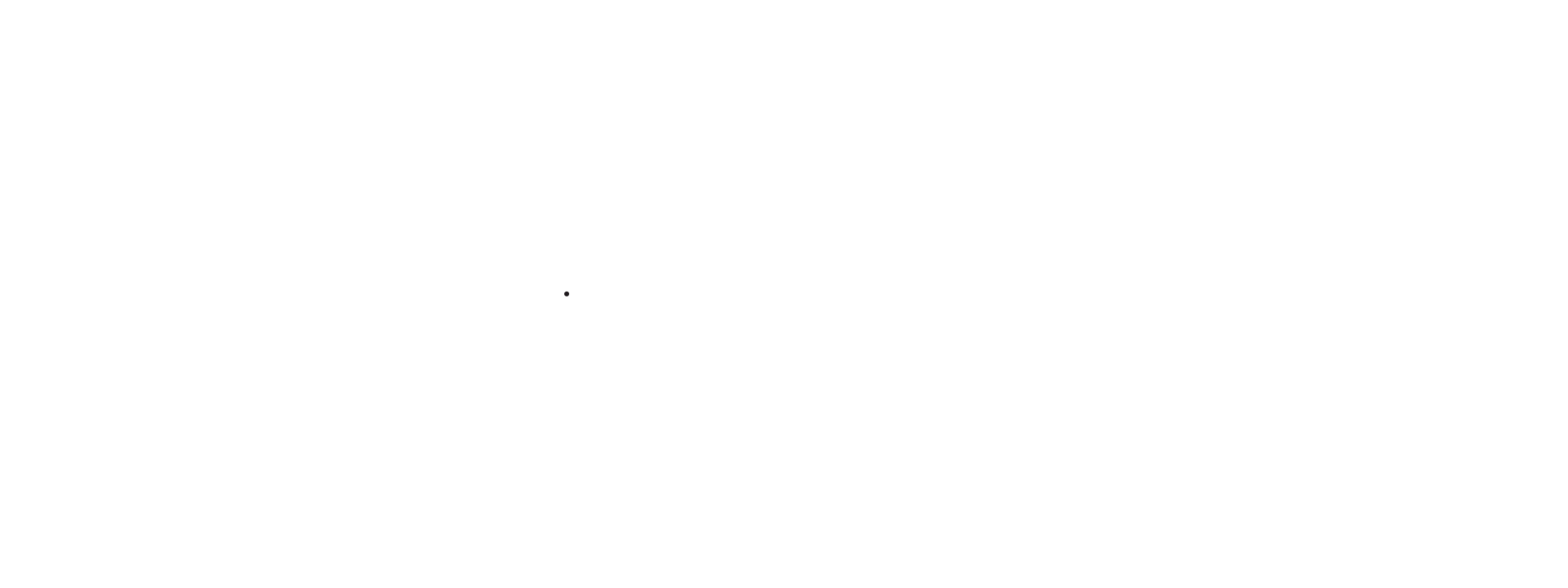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一)
常青回四川,行前留下一摞照片。照片中有学生时期的习作;有十年来静物画的代表作品;有近几年新画的人物作品;更有最近一个时期我从未见过的纸上作品。照片中夹着一封短信,他匆忙赶往别处,却留下了几行真情道白。他谈到渐近中年对生命的感悟,谈到赶回四川去看望病危的父亲的复杂心情,并说:由于这些变化,心态反而沉稳了许多,反倒感到了认命的坦然,“这是一种出逃的感受”。
“出逃”,这个有几分惊愕的字眼,依稀地在常青微光颤颤的画幅上闪现,将这些作品,这些跨度颇大的作品,一下子串联在了一起。表面上看,“出逃”的感觉与常青许多静物作品的精细制作是颇不相符的,但是当我们面对他这个人、面对他的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状态上的复杂现象,以及在他发展路径中被奇特地阐扬着的几个高点,并将之作为一代青年的意识现象来加以审视的时候,便会同意“出逃”这一坦诚的自白。以往常青的画总把我们带到一种对过往岁月的细微体察之中,这一次却向我们指明了宿命的追踪,以及这种追踪之下渴望“出逃”的感受。它划出了一代人的独特的心灵弧线,而那个起始的端点,则是一个少年多敏的内心,是一场关于青春的无名和韶华易逝的敏感之间的无边的追逐。
(二)
认识常青的人,几乎都不去忘记1987年他大学三年级时所画的那张《碗》。那块瓷碗的精到的质感,感动了许多人,并在后来的日子,推动了一个技艺精到的中国静物画派。但是,那悬于画面一隅的孤独、那位于长桌边缘的暗示、以及瓷碗锯痕所隐显的岁月沧桑之感,却开启了静物绘画最感人的一面,是许多同类绘画所远远不及的。
常青这一代人是成长在八五新潮的急骤变化的空间之中。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显示出非凡的活力,社会在迅疾地变迁之中;另一方面,八五新潮的试验精神表现出层层叠进的“反绘画”倾向。这些都将一部分青年尤其是美术院校中的青年逼入了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感觉到了一种无根的彷徨。于是,与八五新潮浪尖上的前卫倾向的弄潮儿不同,这一批青年向着另外的倾向蝉变。他们从现实生活中出逃,从现实之城出逃,以重返传统的技艺方式,借用带着岁月之痕的器具,向着过往的年代、向逆时针的方向逃匿。逃匿与藏身有关,常青将自己藏匿在一个幽闭的空间中,藏匿在一个“它方”、一个他自己“不在”的空间之中。他描绘逝去时代的器物,描绘落满尘埃的岁月,把自己藏匿在浮荡的微光的深处,在那里打磨昔日韶华的凄艳的回光。
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常青沉湎于这一类题材。他所画的旧日的器物,有不知是停是行的钟,有打着锯痕的瓷碗,有老风扇、老相机,有旧报纸、旧眼镜,还有鲜果、干果,所有这些器物,都与时间有关。他熟练地使用各种手法,让器物上落满尘埃,用精致的朦胧营造月光如水一般的弥漫,用微黄的灯光照亮旧日铅华的风采。他着迷地利用道具的台词,描述“人”的隐密的行踪,叙说缺席者的寓言。岁月在这里变成具体的物,而韶华的余韵和陨落,则不断地勾起人们隐密的心绪和生命的感伤。常青几乎达到了古典静物画难以达到的境域,同时,也让自己的“出逃”落入了一口寓义性绘画的深井之中。
(三)
八十年代中期,常青从开放的空间出逃,向着隐密角落、向着自己不在的“它方”自我放逐。他仿佛一部老相机,在一片曝光稍显不足的暗室中,用慢镜头摄下一段一个世纪之前的时光,或者说,摄下被一个世纪所遗忘的时光。弥散的光,带着幽暗的挑逗,在遗忘被唤醒的那一瞬间悄然显象。作为形相,这些器物在黑暗和幽闭中已经存在了很久,现在它突然被照亮,被生活的无名照亮,被“出逃”的本意所照亮。被照亮的不仅是这些器物,而且是器物被遗忘的本身。
96年第一届上海双年展前后,常青开始关注身边的人。他仿佛从器物被遗忘的揭示之中清醒过来,开始从那个深井之中向着真实生活的层面回溯,从他刻意营造的“静物”空间中回到生活的周遭。他画了一批批不同的人物,并让这些人物在水洗的痕迹中静静地退色,却表现出不甘的无奈。就像他的静物中充满着“缺席者”的痕迹一样,这些肖像画总给人一种异样的故事感。画中的人物仿佛处于刚刚被照亮的那一瞬间,还没来得及从迷茫的木然中清醒过来。常青最近画的一系列双人组合的作品,以微暖的黄光,提出性感的暗示。那些弥散着病态的挑逗气息,那种俩人情的暧昧之感,仿佛被某个冒失的闯入者激活,变得格外撩人,格外纠缠,那奇特的困顿和迷茫,似幻似真,被朦胧的微光照亮。
常青没能完全改变这个幽闭的空间,但是,他动起来了。他的笔、他的眼睛流动起来了,他的画流动起来了,他的真实感随着微光轻轻流动。他渴望与文学涵意、与象征寓意、与照片般的晕光效果拉开距离。一方面,正是这些精当描绘的寓意空间,开启了他的某种超验的生命之感,另一方面,这种精当描绘以及可能带来的媚俗倾向,又令天生敏感的常青感到厌弃和无奈。他渴望着从这个“出逃地”出逃,他继续逃向“它方”。
在这里,常青再一次表现出刻划的精微,同时又添加了捕捉的敏锐,对韶华易逝的敏感变成了对生命的留恋和直观。留恋使他的表现更为缠绵,而直观又使缠绵变得大胆而直白。我们似乎隔着厚厚的磨砂玻璃,窥望着只属于两个人的隐密的空间:苍白的面孔,惊悸的手,脂粉的气息……,这些人物更像是一些影子,在上面飘荡着惊悸和无奈的眼神,这种眼神比藉里柯笔下的僧众那带泪的眼神更无望,同时又添加入鱼目一般的木然。我们仿佛不是“看”到这些人物,而是由于朦胧的暖黄的色调,感觉到某种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朦胧的“亲历”之感,让我们来不及看清这一切,就已经为朦胧本身、暧昧本身所经验。常青曾经用布满灰尘的精当的器物,点亮我们某些幽闭的心事,现在又用风尘中的朦胧人物,把我们塑造成“闯入者”,在那里体验某种奇特的经历和想象。
(四)
“动”起来的常青继续着他的“出逃”。正如他的信中所说:大概是人到中年之故,对生命和艺术以及许多事物的认识都深入了些,心态沉稳了许多,作品反倒轻松了。在成都看着那个给了我生命的男人的痛苦挣扎,我开始留恋身边的人和事,珍惜体内的温度。不知您有没发现我比一般的人更喜欢涂鸦,这缘于我好动的天性,我喜欢我的感性对理性的摆脱,这是一种出逃的感受。正是这个给他生命的人的生命挣扎的过程,正是不住地往返于杭州成都,如此近距离地体察此次与它方、生命与死亡,使他从心底里渴盼解放,渴盼一种认命的率真,并把它痛快淋漓地表现在纸上,于是他从老古玩店来到隔壁卡拉OK包厢,现在,他终于来到了街口,他感受到了真实的“出逃”的感觉。
最近的一段时间,常青画了大量纸上作品,碎片般地记录生活中的片断,非常直接地描述各种众生之相。这些速写如此生动,令我想起80年代中期,当常青还是一个大二学生的时候,他的速写就曾经引起我的关注。现在,他经历了十多年的“出逃”,又回生活的周遭,仍然是那样机敏的观察,但多了挑逗性的神情,多了信手而来的涂鸦。无论“婴儿”的系列,还是《卡那酒吧》、《星期五下午》等真实的空间,都带着现象般的记述,带着直面的率真。《阿郎和我在水中》又像绘画日记,又像不断变化角度的观察和自察。这些描绘,从各个角度、各个时间段连缀起一个丰繁而又不定的现象。我们已经不是在“看”这些速写,而是通过这些重复而又跳跃的片断,来感觉生命变换不居的过程。或者说,这些速写本身正在形成某种发生之事,它企图用无数个匆匆一瞥构成我们对事物、对生命的观看本身。
常青仿佛从一个遥远的端点返回。他一路“出逃”,寻找“它方”,却不期望地回返自己的生活环境。这个路径画了一道弧,从那个自我放逐的隐闭空间向着生活的片面回溯,走回了真实生活的周遭。“它方”就在我们身旁,就在我们的生存之地。“出逃”的意义并不在于藏匿,而在于“出逃”本身,在于它使生命永远在路上。正是“出逃”,使常青发现了那个隐秘空间的精微和寓意,也使他从那里得以揭开朦胧人群的迷茫和暧昧,现在常青已经站在了街口,“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
也许生命的本意正在于“出逃”。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