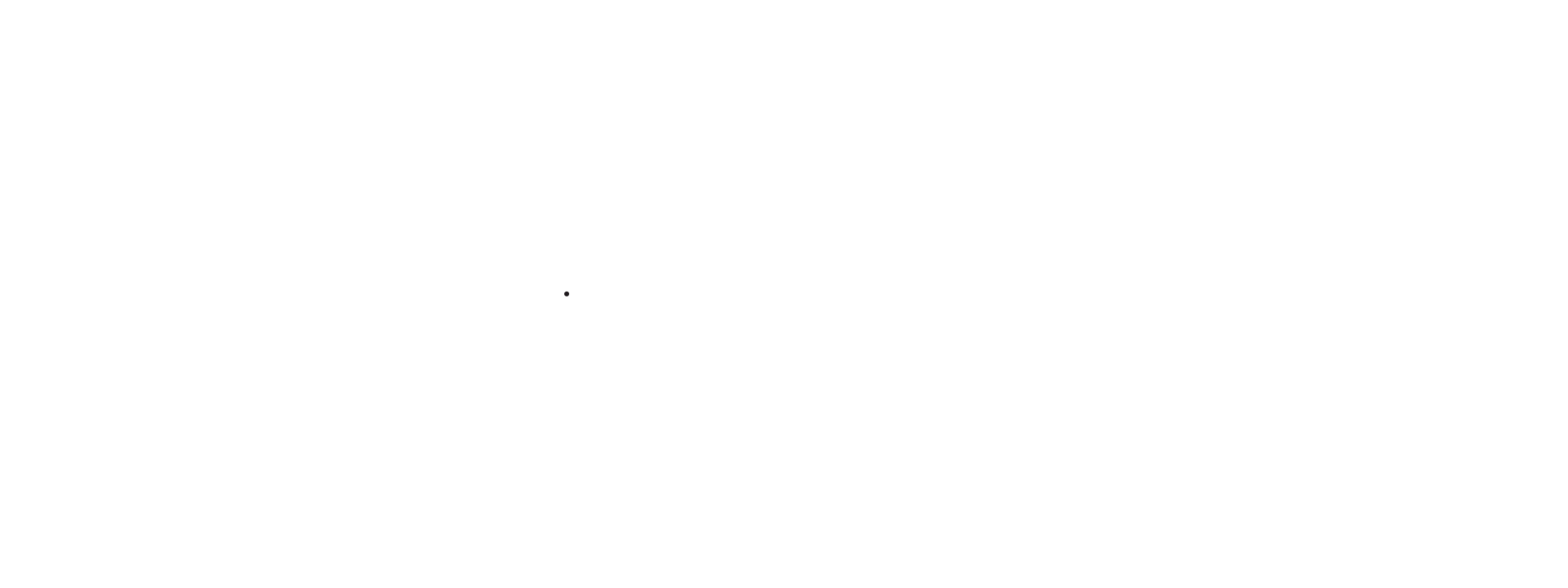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北京29岁艺术家彭斯的绘画作品,提出了自二十世纪早期以来中国艺术家一致面对的众多发人深思的问题。其中包括传统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地位,东西方艺术实践的关系,以及今天从事创作的更年轻艺术家们的“中国性”的问题。
我在这里的评述,最初缘于2010年4月在北京拜访艺术家彭斯工作室时观摩到的部分画作。其间我们品着茶,艺术家现场即兴演奏,他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音乐家,也是一位技艺娴熟的画家。这次造访之后,我在北京798艺术区的一家画廊里看到彭斯的作品,也在《具象研究:重回经典》一书中得到进一步的阅读。又从互联网等不同渠道读到更多的资料,对他的作品有了更深的理解。虽然这些资料中有不少是印刷的或是数字图片的,但对于进行如下的讨论而言相信应该足够了。
I 传统
就彭斯的艺术而言,中国传统艺术是他的作品的本质方面。也像在中国创作的大部分艺术家一样,他的作品明显有着学院派素描和写实绘画的扎实功底。在这种情况下,书法和版画的学习在艺术家的创作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现实主义在他的绘画中非常突出。中国传统艺术中的写实主义具有很多不同的方向,包括人物、山水和花鸟。彭斯几乎探索了所有的这些题材。他并未选择追随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者批判了中国传统艺术,并且着眼于歌颂政治领袖和劳动人民。彭斯同样也回避了二十世纪晚期受西方影响的中国表现主义绘画。
然而,西方绘画的传统对彭斯的影响同样也非常重要。他的作品暗示出他对二十世纪之前西方艺术的深入理解,从丢勒卡和卡拉瓦乔到莫奈等。现实主义虽然不是完全以同样的视觉语汇来表达的,但在那个时代的西方艺术中是一个核心主题,甚至从古典艺术和文艺复兴艺术,延伸到波普艺术、后现代主义以及其他当代艺术思潮。但是,这些来源更多的是当作参考,而不是直接的影响。就像今天从事创作的大部分中国年轻艺术家一样,彭斯更愿意从独立的视角出发,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观念。因此,他不必盲目固守国际上通行的产生于西方的法则。相反,他的艺术代表了古典中西方艺术的交融。与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道,他的绘画在外表和感觉上都不同于历史上或当代的先行者们。
在彭斯的作品中,有人物、山水以及以山水为背景的马。2004年完成的肖像,刻画的是人物上半身,主要是一些年轻男性。在这些肖像中,《玫瑰君子》、《那时花开》、《冠之岌岌》以及《少年红》出自2006年,而《忧来无方,人莫之知》则出自2009年。人物以常规的侧视或正视这些古典姿势呈现在画布上。凝视又间或被偶然出现的一些浪漫情感所抵消—《玫瑰君子》中齿间衔着的玫瑰枝,《冠之岌岌》中立于人物头颅顶端高耸的冠;在后一张作品中,裸露胸膛的黄颜色男子正立着,眼睛直视前方。《那时花开》中的人物神情凝重目视一束鲜花;而在2006年的《少年红》中,人物紧紧抓着胸前的一块红色披肩;在2009年的《忧来无方,人莫之知》中,沉思的男子头戴荆棘组成的桂冠,赋予了典雅的装饰,让人不经意间就会联想到欧洲早期艺术大师的作品。

《玉米地里的牛和驴》
彭斯2009年以来的山水画,例如《孤峰湿作烟》和《肃肃余秋》,准确无误地将中国绘画技巧和西方透视结合起来,开阔的天空中用色彩点缀着山峰和白云。2010年的《怀故土》中,一匹孤独的马置身寂静的荒野,其中也描绘了苍厚劲健轮廓的生命之树以及浸染暗褐色调的大地。在2009年《幕归晚》中,左侧背景中弯曲的树干通过对比强烈的暗褐色和橘黄色色调协和了深邃的空间。这幅作品的画面空间散布着从前景三三两两走过的羊群。一条难以分辨的细线从中间水平横贯画面,向空间中伸展过去,在大的结构结束之际,将视线引向了无边际的远方。在这些作品中,西方直线透视法和中国式的诗意如魔法般结合起来,形成了视觉上灵动的空间。
与《怀故土》可视的风景衬托下的小马相比,彭斯在2009年的《寒江行吟图》以及《骏骨图》中的马匹是完全坚实的形象,似乎刻意地置于明显受中国传统山水画影响的荒寒冷寂的空间前景上。这些马匹造型俊朗,且有各自与众不同的特征。这些马匹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中,很容易联想到十九世纪欧洲或美国画家的作品。它们也会被善意地同中国十八世纪绘画中西洋画家或受西洋画影响的画家笔下的马作比较。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彭斯将传统中国和西方绘画手法相融合的努力,让人想起郎世宁(1688-1776年),他是意大利耶稣会士,供职于中国三代皇帝的宫廷。郎世宁给那时中国人传授西方绘画,而且又向他们学习如何按当时中国艺术家的理念来画画。作为在中国的西方画师,郎世宁画的乾隆帝(生于1711年,1735年-1796年在位)肖像,以及他的马和风景,因为融合中西绘画而提供了成功的范式。就彭斯的绘画手法而言,我相信他一定参观过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郎世宁作品。在这些画作中,包括郎世宁所画的乾隆帝肖像、山水《海天日出图》以及描绘皇帝骑在马背上、或者骑马狩猎的不同画作中的马匹形象。这并不是说彭斯模仿郎世宁,而是他的作品构图及风格上显示出了出色的才干,在他所创作的这类绘画作品中可算是出类拔萃。他选择当下时代的年轻人物形象,往往用一种浪漫的手法来表现,反映出与三百多年前宫廷画师完全不同的目的,后者有责任宣扬皇帝的尊贵以及以皇家的生活。但是彭斯对于在同一画面中运用中西方绘画手法的兴趣,特别是他那种面对人物的理想化的处理手法,与早期画家的作品有某些相似之处。
II 现实主义与抽象
从上述所引用的彭斯作品来看,显然在理解他的作品时,具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且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内涵和意义。特别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甚或同一时代从事创作的那些艺术家的作品而言尤其如此。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画家的作品同彭斯的作品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清楚地分辨出来。在两种情形之下,现实主义是随艺术家主观目的、对象、材料、笔触以及细节范围而不同程度的表现的问题。就像艺术史学家琳达?诺克林对现实主义的论述:“在绘画中,不论艺术家的眼光多么诚实或多么有创新,可见的世界必定被加以改造,以便在二维画布上来经营它。因此艺术家的感受也不可避免地以材料的物理属性为条件,运用知识结构和技巧,甚至是他的笔触,从而传达三维空间,并形成一个二维的画面。”
对于彭斯的绘画艺术,从对自然或人物或马的具体表达上而言,又并不完全是现实主义。相反,它们都是艺术家自己融会贯通传统中西方艺术经典的语言构建起来的,从这一点上讲其实是任重而道远的。在中西方艺术之间存在的一些根本性差异也必然要克服。例如,传统中国山水画中注重书法式的笔法,依靠艺术家精深的内在精神指导去书写线条并经营画面。相反,西方绘画中,特别是在文艺复兴之后,关注视觉上的真实存在。而在色彩运用方面有着更大差异,中国人喜欢微妙的、层次丰富的水与墨,而西方画家倚重更广泛的色彩,更强烈的过渡。对自然的不同看法也成为融合两种传统过程中的关键因素。中国审美中,自然更多的是胸中的丘壑,而大自然在一种积极的意义上被表现成玄远的山水。而在西方的审美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被刻画成彼此抗争和对立。中西方现实主义之间存在这些看似根本的差异,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现实主义实际上能否准确地概括彭斯的作品。他的绘画作品也可以理解成一种抽象艺术吗?看起来艺术中的现实主义永远也无法同抽象截然分开,不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艺术中。书法在中国绘画中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抽象导向。这种在书写激发之下的抽象倾向在某些西方现代画家的作品中也非常明显,例如约翰?卡格、弗兰兹?克莱因以及罗伯特?默兹威尔。并不像美国批评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错误地理解的那样,抽象与现实主义这两者相互排斥。格林伯格提出,抽象艺术是一种可以识别的影像被“大体上与描述性内涵(或者隐喻)完全脱节的色彩、形状和线条之间关系”所取代,让观众无法在画面空间中区分出感兴趣的焦点。从格林伯格的这种意义上讲,彭斯的画作并不是抽象的,而是有非常具象的存在。但是在彭斯作品中可识别的具象,如人物和风景,都是他融合中西绘画的表现手法的结果。而且这些手法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媒介。在这方面而言,彭斯肖像人物以及风景绘画的构图,仍然保持其独有的风格,且传达出他所追求的格调和意境。当然,它们可以被理解成具有某种隐喻,能够在观众的体验中唤起对自然的亲近或心灵上的感知。

《肃肃余秋》
III 中国性
如何解决中国当代艺术中所谓“中国性”的构成这个问题,可能是今天中国艺术家心中最关注的问题。几乎任何解决这一疑问的努力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彭斯选择了利用传统中西方艺术这两个资源。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为西方艺术赋予了如此突出的地位,因此承担了被他的中国同胞贴上“西方艺术”标签的风险。另一方面,他又运用油画材料捍卫传统,又承担着另一种风险。那么多出色的中国艺术家已经成功地转向了当代艺术手法来表现自己的中国性,被人贴上传统主义者的标签还会有机会吗?
例如,独立实验艺术家蔡国强(1957 - )在对“中国性”的追求中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同而且更加激进的道路。在参照中国传统宇宙观、道家、东方神秘主义以及风水等的同时,蔡国强用自然力(例如风和火)、壮观的焰火以及中国人发明的火药来进行实验。他的自画像(火药和布面油画,1985),具体说明了他对火药的使用。艺术史家巫鸿说到,“爆炸的痕迹可以看到不同的形式;人物周围的区域是黑色的,而人物的轮廓非常模糊,因为火药燃烧留下的痕迹而突出出来”。在这种情形下,艺术家用自己的火药实验对1980年代中国的社会环境提供了一个社会性的诠释。
彭斯的目的完全不同。他并没有表现出像蔡国强作品中蕴含的那种社会或政治诠释的兴趣。他着眼于绘画艺术的本质,用他自己的方式来解决中西方艺术的关系。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任务,而且对于一位仍然在构架他自己持久的艺术平台的年轻艺术家来说非常合适。他显然投身于触及观众心灵的艺术创作这一艰巨任务中,并获得了令人关注的成果。他的绘画作品已经吸引了画廊和收藏家的浓厚兴趣。上面提到的两幅作品已经在最近香港佳士得亚洲艺术拍卖会上获得了成功。种种迹象表明,他的作品可能在商业上已获成功,部分原因是因为这些画作精美耐看。它们吸引了艺术界之外仍欣赏高雅艺术作品的人们的关注。希望他在商业上的成功不要过快,从而导致他遗弃了自己非比寻常的艺术潜质。我们能够从这位艺术家身上看到的是在未来中国当代艺术中为那种“中国性”的观念作出巨大贡献的起步。有充分的证据显示,不必担心他在未来成长和进步的过程中摒弃传统。或者,也许他对传统的学习和借鉴从后现代主义的意义上讲,实际上恰恰成为某种对艺术进行超前思考的形式。
1、 《具象研究:重回经典》(Revolutionary Realism: Research Representational Painting Reenters the Classics )(北京,2010年)
2 、关于彭斯作品的其它观点,参看理查德?舒斯特曼的《艺术与社会变革》(Art and Social Change),刊登于库蒂斯?卡特主编《艺术与社会变化:国际美学年鉴》(Art and Social Change: International Yearbook of Aesthetics)2009年第13卷,第16-17页。彭峰《辉煌的忧郁——解读彭斯的绘画作品》,引自《风---彭斯,2005-2007年》(北京2007年)
3 、在郎世宁帮助下,中国学者年希尧写出了《视学》,就中国传统和西方的透视问题来讨论西方透视学。该书发表于1735年。这是中国人首次讨论西方艺术技巧的著作。
4 、琳达?诺克林,《现实主义》(Realism)(纽约企鹅出版社,1991年版)
5 、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抽象与具象》(Abstract and Representational),载于《艺术文摘》(Art Digest) (1954年11月1日),重印于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文论集》(Collected Essays),第三卷,约翰?奥布赖恩主编(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6 、巫鸿,《论中国当代艺术家》(On Contemporary Chinese Artists)
7 、2006年的《冠之岌岌》和《那时花开》均在2010年5月30日香港佳士得拍卖行拍出,拍品编号为1722和1723,出售编号为2808。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