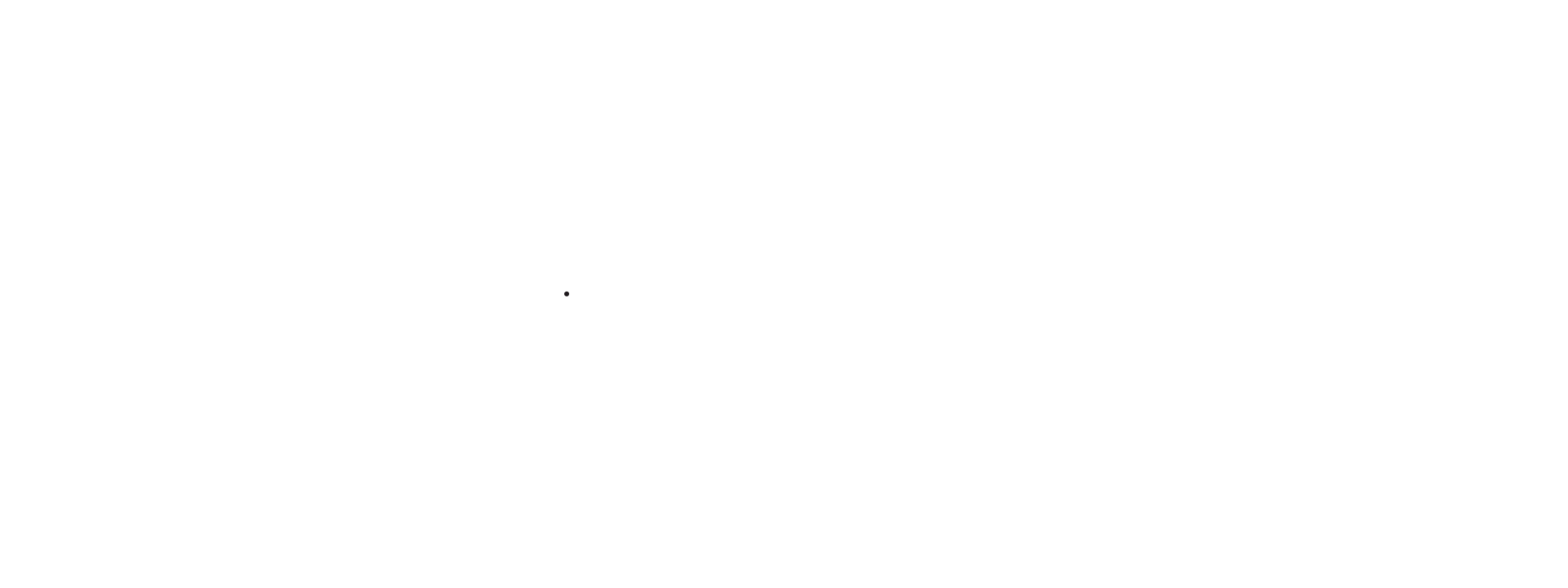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 蜀道”之难
写实绘画在今天之难,难在有太多可以比较的参照。比较当代艺术的其他门类,它的标准太明晰,限制也太多,且不论我们熟知的经典高悬在博物馆的殿堂之上,这是一把被观众随时用来丈量画家的尺子,还有更加 “写实”的摄影术,时时提醒着画家,如何在图像时代让绘画有自身的领域,同时又赋予新意。与红舟同龄的画家,大都在写实这条路上开始艺术的启蒙,而能留下来,并在此领域里有成就者却寥寥无几。因为难,因为太难,即便穷尽一生,也未必能有所建树。红舟却偏偏选择了这样一条路,一条类似于“蜀道”的艰难之路。
在红舟从艺的道路上,有太多可以选择的路径。凭着四川人对时风的敏感,也凭着他那出色的手艺,本可步履轻松得多,成名时节早得多,可他偏偏选择这费时、费力的写实绘画,又是那种一眼看去最平凡,最不容易出新的方式方法。这种平实之中的华彩,当年只有维拉斯贵支能够做到。这样的艺途,说它堪比“蜀道”是不为过的。
红舟给我的短信里说到自己会这样说:“我不是一个很生动的人,画也受牵连……”他总是这样,无论在什么人面前,总把姿态放得很低。这种来之骨髓里的谦虚和诚恳,以至于他在面对自己的画作时总有一点诚惶诚恐。因此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得意忘形的样子。即便在他亮出画作,引来同道发自内心喝彩的时候,他也会笑眯眯地把你推开,好像那画中依然有太多的“羞涩”之处会被你看出。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他接受褒奖的特殊方式,也是他对自己“煎熬”出的东西短暂地认可。
怎样才是一个生动的人?一个很生动的人?红舟心里知道,并且对此耿耿于心。因为,他认定自己“不生动”也罢了,可是“画也受牵连”,他便放不下。是不是因为此,他选择的朋友个个都是活灵活现的生动之人,如常青、小冬。只有他们纠缠在一道“舌战”时,我们才看到红舟的另外一面,那种在“防御”之中的机智和幽默,甚至有几分“小坏”;也是不是因为此,他并没有把自己高超的写实能力变为精雕细刻的描画,而是毫不掩饰的用自己的画笔和态度表达着对维拉斯贵支、哈尔斯这类画家的敬意。并且无论世风如何变化,他坚定的以自己的画笔和行为去实现他对绘画的理解。
仅就一般的说法,画一定是画家性格和阅历的综合体现。那么,红舟认定自己“不生动”,却偏偏向往形意潇洒的绘画,便陷入一种“自寻烦恼”的矛盾之中。这是红舟自己给自己下的结论,也会引导我们以这样的“先见”来审视他的人和画。
生活里的红舟不是那种霸气十足的人。在他的家中,父亲过世之后,除了他,全是女人——他的妈妈和妻女。他得用大半的心思来尽孝道,夫职和父爱。对待朋友和同事他谦和礼让,聚会的场面上总是甘当“配角”,从不抢他人的“戏份儿”,对待学生他也是有求必应,几近那种没有脾气的“好好先生”……日常生活让他不知不觉地多了一份细心的体察和做事为人的周到。其实这是画家的福分,尤其是那些偏爱“笔意”的画家的福分,因为在那纵横驰骋的挥洒中,不知不觉地蕴含着一种内在的细致。这种细致,不雕琢、不刻意,是一种来自于心的体悟和日常习性的指使。
红舟是那种暗地里使劲的人,甚至有点“举轻若重”。面对画布的时候,他总是紧锁着眉头,绝不会有情不自禁吟唱的时候,也看不到他开怀大笑的瞬间。他的画里展示给我们的洒脱,应该是他呕心沥血而得到的结果,他把过程中反复煎熬、千迴百折的艰辛通通留在了观者的视线背后。也因为我们熟知他做画的过程,才对他笔下的犀利和洒脱有着一份格外的敬重。相较之那种信手拈来、才华四溢的画手,红舟的华彩多了一份醇厚。他笔中有锋,却不咄咄逼人;画中有气,却文质彬彬。他的画不愤世嫉俗,是因为他识得平凡之中的“箇中三味”,仅用他的笔,让平凡多一点心跳。
1985年我在赵无极学习班时,曾问过一个很幼稚的问题:马蒂斯画画时应该是很轻松的?赵先生回答我:不,他是把愉快留给观众的画家。多年后我才懂得作为一个好画家的道理,明白“六法”之中的“惨淡经营”之说,还有那句“呕心沥血”成语的含义。
画家的“难”,只有画画的人知道。哪怕是形意潇洒的画家,在他作画时心无旁骛,信手挥写的背后,仍然有画外的潜心研习和日复一日地苦修。红舟当是这样的画家。
红舟有原则,也偶有脾气,但更多的时候他是温良与谦让。他在酒桌上难得的“豪饮”,一定是遇到了知己,满脸赤红的他会忘了平时的内敛。创作一张大画会让他减去十几斤的体重,这样的情景或许只有与他合作的老友才知道,也只有他的老友才能从他客客气气的处世方式中,知道他也会因为画到深处,将自己遭遇的不顺和内心的烦恼“迁怒于人”。其实,这样的时候,红舟是个很生动的人,他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流露出他性格中的另一面。
红舟身上没有那种大而无当的习性,他的性格不能用“豪迈”一词来形容,画也不是 “肝脑涂地”般地壮烈。他不是那种平时显山露水的人,却能在关键时刻堪以重任。大凡学校里有重要的绘画定件,他总是不二人选。只要有他在,多重要的国家定件便有了八成的保险。正像那两幅《启航》的历史画,都可谓是“受命之作”。每当这样的时候,许江“老板”定会想起能“横刀立马”的何红舟来。
是的,没有了赵云,谁能堪当诸葛孔明的“抱负”。
我觉得红舟向往的,是那种内敛的潇洒和生动,是那种赵云式的风采。刘备的五虎将里,赵云不是戏份与传奇最多的人,但那驰骋在百万军中单骑救阿斗的故事却是三国演义里精彩传奇。
说到这里,我觉得红舟的人与画并没有互相悖行。相反他是如此诚实地将自己性格中的多重性呈现在画布上,并老老实实地叙述……他的喜悦,应该是在他的画配上外框,挂上墙面的霎那,霎那之后又是无休止地内心纠结,一如他所自嘲的“画不好”,然后便是下一个轮回。
红舟经常调侃自己,“除了画人物,别的不会画”。实际上在今天的绘画格局中,人物最难画。首先,因为在西画的领域里,人物画的成就实在难以超越,其次,因为人的具体性,以及身份的指向很容易落入写实主义的“叙事”陷井,同时还面临着摄影的挑战。因此,西方近现代关于绘画本体的探索大都避开人物画。红舟深知美术史,深知面对这一命题的困境。
相悖的是,往往困境之时,便有希望所在。20世纪,几位让中国画界心跳的画家,都恰恰是逆流而行的人物画家。在中国,人物和主题性的绘画已有百年的历史,但较之西画的高度尚有攀登的空间。因此红舟的选择和定位,是建立在对自己、对国情的深刻了解之上,同时他坚信写实绘画仍然有很多的可能性。
红舟绘画的题材多半是肖像和人体。这个题材从他1988年毕业创作一直延续到今天。在这样一个看似狭窄的领域里,他有自己认定的抱负。他的画有情节,但决不止步在写实性的叙事上,而更多的是借此题材表达他对油画语言的理解,以及对当代人日常生活状态看法。
红舟的画十分在意笔下对象的精准,同时警惕着由于过度精确滑向描摹的边缘。因此,他画中的形态,从不流于小笔的精雕细琢,哪怕是刻画的再精致,也是用大笔“带”出形的精准,是在“绘”的过程中,用笔“带”出来的洒脱,并在寻求形态和笔锋双双饱满的建构之中,达到他心中对绘画界定的高度。这样的画是最难的。好像董其昌、也好像王蒙的绘画,不险峻,不张扬,也不靠奇山怪石、奇葩异草的烘衬,而是以温厚内敛的笔墨学养,平和,醇厚,有节制地诠释着对绘画的理解,这才是艺术中的高难境界。
其实画家所关心的始终是怎么画,怎样描绘被我们司空见惯的事物,展示着他是如何看,看见了什么。在绘画史的链系中,画家一方面传承着观看和表现的惯性,另一方面志在冲破这种习惯,而寻求一种新的可能。因此,从专业的角度上说,画家内心深处的话,是对其他画家所说的,是对美术史所说的。
写到这里,我在想,生活里怎样才是一个生动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又如何用好与生俱来的性情品质,并将它化为笔中词汇铺写到画布上?红舟不是那种能在人群中振臂一呼引来关注的人,但你如细细打量、揣摩,你一定觉得他的生动另有天地。或许,学问之道,不一定非得是另辟天地,传承演化,也同样重要。艺术研究,不一定得回回更换话题。更多的情况下,我们得知道,怎样的话题有可能既承接上文的脉系,又有下回分解的可能。我们能不能对一个古老的话题“接着说”?又如何演绎出新的解释?所以,红舟的绘画之难,难在不紧要出色地把握传统绘画的精髓,更难在如何“用活”这一传统,使之活在今天的文化语境里 。同时想想看,在我们这个躁动的艺术领域里,有多少人甘于在僻静的一隅,攀行这绘画之中的“蜀道”呢?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