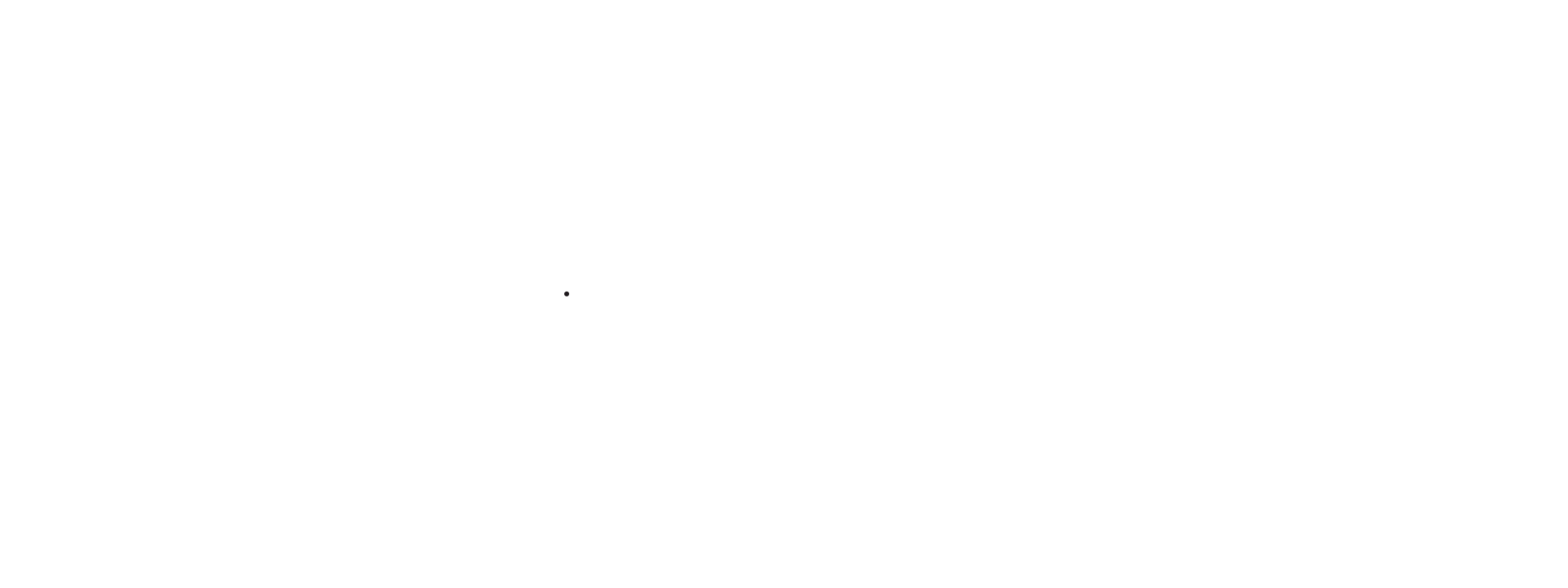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王华祥可以被称为思想家、教育家、艺术家,如果你愿意还可以称他为建筑师,你不认识他那是你的眼界问题。说他是思想家,是因为他每日在微信上发《王的词典》堪称箴言,用犀利的文字剖析历史、人、文化和信仰;说他是教育家,是因为他像博伊斯一样死磕中国艺术教育机制,“将错就错”的教育观念风靡90年代,后又只身创办艺术私学“飞地艺术坊”,其反向教学法教出来的学生让高大上的美院们隐隐作痛;建筑师的名头更是自不待言,他设计的万圣谷美术馆依山傍水,有外有内、可观可居。这个较真而逍遥的贵州汉子,啥都想拿起,啥都拿得起,啥都玩得起,很容易让内心不定的人羡慕嫉妒恨。
我觉得,有一个更牛逼的称呼才能配得上他:活人。在一个僵尸和残废横行的时代,王华祥保持着健壮的肉体和笔直的精神,是艺术圈不多见的大活人。我跟王华祥说打算用“活人”这个词来描述他,他立即回复:再牛逼的死人都比不上最怂的活人——其实这句话已经把我要写的全部说完了。
世人谈起王华祥,或说他叛逆不羁、个性彰显;或说他为人耿直、有情有义;或说他功底深厚、素养不群;如此等等,让他在圈子里变成传奇故事,也让许多熟人无暇顾及他的“源价值”。在我看来,艺术、思想、个性只是他给我们提供的表面热闹,让人喜欢谈论他,让人喜欢琢磨他,但他想提供给我们的断然不是故事,而是他的态度:在做任何事情之前,首先要确认的是自己是个活人,不是活人,哪来的思想,搞什么艺术,谈什么个性。从他开始接触这个世界,到他当上艺术家,到进入中央美院,再到今天功成名就;王华祥一直保持着一个极其牛逼的状态——活着,从年少时的勇猛、叛逆、较真;到今日的回归、谦卑,所有的精彩只是他不同时期、不同环境下活着的证据而已。

《风往回吹01》
王华祥生于贵州一个贫穷落后的小镇,据说小镇上只有十几户人家。从那时的场景来看,恐怕王华祥自己绝不会想到日后他在中国艺术界掀起的波澜。但世界的奇妙之处在于,经济上的贫瘠,却意味着另一种丰盛,上天从来都是如此公平,甚至是慷慨。王华祥年幼时生活里没有艺术,但却有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天空、草木、岩石、河流,以及它们的壮美引发的最质朴、最真实的感动——其实这就是人“活着”的感觉,简单,却是最极致的满足。许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他的幸运:绕过了那些以文化的名义矫饰的二手经验,没有在最稚嫩的时候被文化阉割。此后,他便一直坚信、坚守肉体真实的感觉,穿越如同海妖歌声一般的艺术、文化、知识而不曾睡去,这便是我所说的“活人”。
生命在这种状态下开始,造就了王华祥务实、较真的性格,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一直强调“技术”。技术是一个无法容纳巧言善辩的东西,真实而公平,在技术面前人可以获得一种平等,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会说也不行,除非你真的在这上面倾注了生命。技术如同数字,最不兼容谎言,如同上帝未经篡改的手稿。事后证明,不善工巧的实在,成为王华祥死里逃生的大智慧。1984年王华祥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版画本身带有极强的工艺色彩,而工艺的核心就是技术,它比架上绘画有着更强大的表达力。这种看起来不“艺术”而且又脏又苦的活,正对了王华祥的轴劲。艺术和种地一样,只有舍得力气的人才能有好收成——他的版画作品《贵州人》获第七届全国美展金奖——关于全国美展金奖究竟是怎么个牛逼法,读者自行百度。王华祥留校后为版画系开设一门叫做“一幅肖像的三十二种刻法”的课程,听名字就知道这是“简单招数练到极至”的武学路数,这种看似笨拙的套路暗示着他的靠谱:如果想说事,必须先学会说话,哑巴、口吃、大舌头都不行。技术才是最能传达肉体经验的通道,没有深埋在地下牢靠的基石,哪里来的凭栏仰望。从这个角度看,王华祥看似个性张狂,实际上内心非常谦虚,他甘于沾满泥土的务实、扎实;而不去妄谈空虚飘渺、人力不能所及的虚妄境界;只有先拿得起,然后才能谈放得下,那些型都画不准却说要超越“技术”的人,才是真正的狂妄和怯弱——技术的难度人尽皆知,惟有勇气者才敢向虎山行,不入虎穴,便没有后来的“抱虎下山”。

《风往回吹24》
中国人做事,习惯于避实就虚,绕路而行,并将这种鸡贼自名为高度,是故“技术”这种立场坚定的东西,如同那些说话耿直的汉子一样不受待见。让我们傲娇了几百年的“中国文化”号称崇尚“自然”,其实崇尚的是一个山寨版的宇宙,它不将人引向造物主手中真实的宇宙,也拒绝真实宇宙中万物的本性:以道德的名义禁止情欲,以高雅的名义矫饰景色。血气方刚的小伙子不能想女人叫文化,长得好好的植物掰弯了叫文化,有话不直说叫弦外之音,背地里互相搞叫谋略……当这些矫饰以文化的名义成为共识,置身其中的人便几乎断绝了与真实客观世界交流的能力,并以虚为荣。当人被这种文化境界吸引时,便开始两脚离地,而真实的情况是,如果人的肉身真的进入宇宙,必死无疑,因为那里连氧气都没有。直至今日,那种处于催眠状态半死不活的文人雅士,仍然不鲜见;而忙于生计的贩夫走卒们,却在大地上步履坚实。王华祥是置身于文化死地,却坚持活着的少数派,他就喜欢实在的东西,技术,肉身、土地、钱……活的油光闪亮,让那些无法仰仗权力将他掰弯的人们愤恨不已。
九十年代以后观念艺术的兴起,让本来惯于务虚的知识人、艺术家火上浇油,又一次集体升空,只不过“境界”换成了“观念”——其实与西方当代艺术中说的“观念”没几毛钱关系。这段时间的王华祥对艺术界非常不适应,却又无处说理。在中国人陷入集体癫狂的时候,如同面对一群醉汉,说啥都白搭。但此时王华祥最牛逼之处,不是以一个保守者的姿态远离,责备;而是又一次下定决心进去看看,只有看过、试过才知道观念艺术到底多牛逼。于是,这个一直推崇“技术”的人突然一个猛子扎入当代艺术,搞起了行为和装置。让无数“正人君子”深恶痛绝的装置作品《欲望中国》就是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欲望中国》简单理解就是一个“鸡鸡”主题展,有雕塑有绘画,全是景色各异的大阳具,有的穿破铁丝网如知识分子一般孑然独立;有的如红色纪念碑一样向前向前向前;比较代表性的作品是一个看似半死不活的男人躺在地上,而下身却如树枝一般长出许多亢奋的阳具,有些因为力不从心已经折断。现在这件作品被放置在他的美术馆前面的水池里,不久前他在微信里说周围的阿狗阿猫很能生。这件作品非常切题,它把中国从文革到市场经济以来的各种癫狂状态生动表达了出来,文革时期的政治欲望,市场中的贪婪,如同打了春药一样的鸡鸡,看似坚挺实则力不从心,只因为这种亢奋并非来自生命体本身,并非造物主的本来意愿,所以叫做《欲望中国》。王华祥通过这件作品表达了他对躁狂时代、躁狂基因的反对,却被那些同样自诩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狂骂——不过当他们以道德名义讨伐王华祥的时候,自己也变成了那些阳亢的鸡鸡,而王华祥只好在边上一边擦着脸上的唾沫一边看乐。

《风往回吹33》
“鸡鸡”展之后,王华祥看懂了“当代艺术”到底是个啥东西,以及以“当代艺术”名义批判时代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啥东西,一脸唾沫星子反而换来了一种踏实。此后一段时间,王华祥明显淡定了太多,看起来他更加坚信原先的方向。在全民奔向当代艺术的时代,他公开、大声、自信地回到古典。对于一个真正拿得起技术的艺术家而言,“古典”绝对不是外行理解的一种情感上的依赖、品位上的正确、文化上的神圣,这些都是票友的错觉。古典绘画的奥秘,在于在那个有限的视觉技术条件下,最大限度地通过视觉进入真实世界,它蕴含着一种能够真正通向我们无力触及的、真实世界的道路。技术的本质是理性,而无数人尚未锻造好这枚钥匙便已宣布这里是死门。这时,他的《风往回吹》系列诞生,从名字到绘画语言,都可以看出他已经真正打开古典绘画的大门。这批绘画以一种古典风格的寓言场景出现,描绘了一群性格各异的人物。乍一看平淡无奇,而一旦进入发现大有意思。这些人物的表情既不是我们熟悉的古典主义中那种庄严;也并非战后现代主义绘画的萎靡失落。我想,他意识到真正复杂的人性状态,在艺术史中被折叠起来,只看见封面和封底;而他要做的,就是在绘画中将其重新展开。于是,这批绘画呈现出了人性中被遗弃在角落中的部分,尴尬、怪异、无聊、莫名其妙甚至有些低贱的精神状态,但真实、亲切、可爱,令人毫无厌恶感觉,这正是王华祥此举的厉害之处。创作这批作品时,王华祥已接受基督信仰,以他以往的性格,非常容易借上帝的名义敌视自身及他人的人性缺点,从而产生审判他人的心态——无知的我就曾陷入过这种境地。然而,在深刻洞察了人性的复杂之后,王华祥做出了令我出乎意料的反应,他不再用“罪性”这个词来描述人性的弱点和不足,而是将其看作一种“常态”——一方面冷静揭示出人的愚昧无知,一方面却又对其充满善意和理解,同时也宽容了自身人性的弱点,这也是近几年他活得越来越好的原因。
王华祥始终有一种本能的“求真”意识,而被中国古典知识腌过的文化人往往抛弃求真而去求善,求美,多半不得要领,半路死机。一个人能够沿着求真的道路走来,在中国复杂诡异迷宫般的艺术、政治、情感、人性中穿行而不致迷路,一直走到信仰,而且是理性状态下的信仰——在感性虚无的中国文化土壤中达到理性的信仰,这是何等分量,过来人自然明白。在最新的作品系列《等待花开》中,那些纠结、挣扎、茫然的人们包括他自己被安放在花盆中,看似囚禁的土壤同时也正是生命的来源——这个显而易见的寓言场景或许就是王华祥对所有问题的答案:人的命运,生于大地,困于大地,进入大地;而无论你我多么愚昧,在园丁的眼中我们都将开出花朵,而最终谁开得最鲜艳,不仅未知,而且值得期待。任何自以为是的断言、预测都是枉然,不如抛却那些虚妄的想象,活在花盆中就好。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