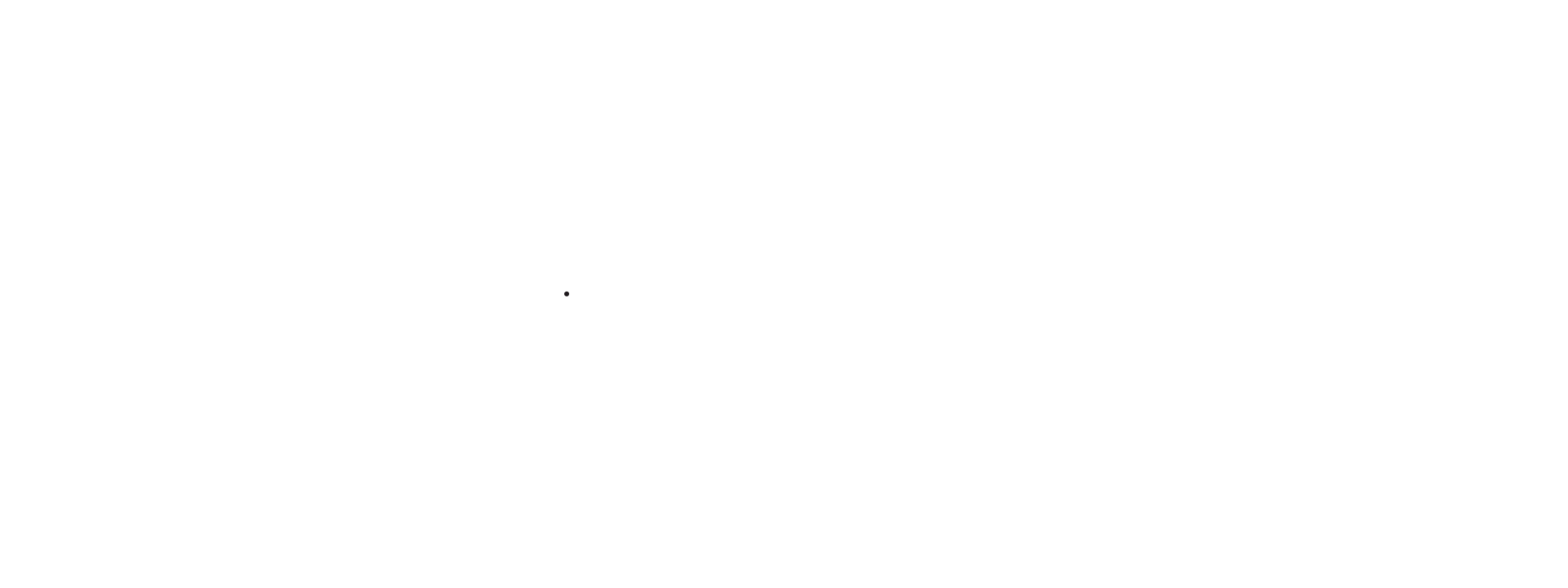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从“罂粟”说起
“罂粟”是井士剑在乡村田野间邂逅的一种植物,也是他自1993年便开始持续关注的一个创作题材,美艳与危险之间的张力,昙花一现式的从盛开到凋零的不确定性,都让井士剑冥冥间感应到这种植物与当代社会的某种相关性。这或许也是“罂粟”最初吸引他注意力的原因所在。纵观二十余年间井士剑关于罂粟的描绘,我们也不难看出其画面的变化,以及这期间艺术家思考的演化过程。
“罂粟”在井士剑早期的画面中,更多地承担了一种“社会学”式的阐释功能——***、高速公路、汽车,以及骷髅头等等意象常在他的画面中产生并置,以启迪一种参差的观念性表达。但随着不断与“罂粟”对话的深入,我们发现井士剑开始更多地依靠笔墨来完成关于“罂粟”的描绘,在摒弃惯性思维构架的同时,着力于还原一个人们可以在自然中看到的“物象”,这是一种对于“视觉真实”的挖掘,也更多地将阐释的主权交还了观者。

《The Blooming Flower》
这种转变实则对应着艺术家在认识论及方法论层面的转换:从一种以艺术做为表达的媒介,转换而为以艺术做为思考的方式——“罂粟”在这里,不再做为艺术家个人主体性的表述承载,而是成为了一种对象,艺术家经由对于它的观察与描绘进而去思考身边切实所处的现实。这种凭藉对于类似世界神经末梢的感应,进入到艺术的直觉认知的方式,让井士剑的创作摆脱了宏大叙事的陷阱,也避免了“概念”本身的遮蔽性,可以直达视觉与知觉的真实。
回到自然的本初
经由“罂粟”的植物性,井士剑开始更多地去思考“自然”。自然(NATURE)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拉丁语系中,都有“万物之道”(THE COURSE OF THINGS, NATURAL CHARACTER)的含义,也都同样地指向了事物的原初和本真。而通过一系列现场的、直观的对于“罂粟”根系性的描绘,井士剑展开了对于“本初”的追问和探寻,并由此思考个体性的创作与生活世界的开启之间的共属关系。
井士剑认为,今天的世界,存在着过多的“描述”,而只有回到“本初”,才能够真正地让眼前的对象从一个划定的概念,或者说模式中解脱出来,恢复其最为原初的独特性,他的创作,也便是试图将这种“新鲜”直接带入到无言的凝想之中,在这样的基础上,去重新让观众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能给这个世界提供些什么。这种努力,也正如怀疑论者伊壁鸠鲁在《自然与快乐》中所强调的态度——还原事物本来的样子。

《The Swaying Flower》
我想这样的理念,也应该是井士剑“罂粟”系列独特性的来源——摒弃了当代艺术中常见的观念性的牵绊,却又显然与单纯的静物作品拉开了距离。因为他对于“罂粟”的描绘,并非简单的模仿,而是将自己对于这一物象的综合认知还原到观众的面前。在创作的过程中,事物、现象和语言的片断被画家以一种活跃的思维聚集在一起,因而产生了一种揭示性的力量。这也让井士剑的作品超越了经典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的概念,而具备了未来的指向性。
摇曳的自然
将目光回归到自然的本初,也让井士剑发现了自然的“摇曳”。而“摇曳”也的确是只有当一个艺术家的观察,能够真正地从整体的、宏伟性的叙事状态,还原到一个切身所在的情境时,才会发现的一种情状。我们当然不会说群山摇曳、江河摇曳,“摇曳”只对应于草木、花朵,对应于我们身边细微的枝节,回归本初的探索,也让井士剑在身旁的细节中通达了普世性的观念。这与古人所谓,观一落叶,可知天下秋的智慧,似有异曲同工之处。

《Flowers in Red》
井士剑所谓的“摇曳”,首先会让人联想到“轻”,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谓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它里面暗含着一种“动感”,也意味着一种“缺失”,一如“罂粟”在短时间内所经历的盛开与凋零,在与之对话的过程中,井士剑也发觉到以往文化中所言谈的关于自然的伟岸、浑厚,和博大,已经伴随着当代文明的进步,社会的发展,而快速地消失殆尽,人类对于自然的剥夺、摧残,让自然的本体在当代已然成为充满摇曳性的存在。
在观察到的一种“自然性”退化的同时,井士剑进而也发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自然观”以及藉此而产生的一切文化,在被置入于当代语境的时候,又何尝不是摇曳的?“自然”在当代成为了我们的“景观”,我们并不与它同在。而那种以人与自然同生共长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关系为基础的一系列澄怀味道、卧游栖居等传统的精神体验,也开始与当代人无缘,而只能成为我们今天的一种文化假想。
结语
我想“摇曳的自然”应该是一把解读井士剑画面的钥匙,凭着它,我们可以品读出井士剑作品中关于个人与世界、理想与现实、传统与当代的一种自然性的思考。与此同时,井士剑也非常清晰一个艺术家的本分——提出问题,而非解决它。所以,他将自己观察到的“自然的摇曳”呈现、还原在画面中,不做评判,只启发并期待着每一个观众自己的解答。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