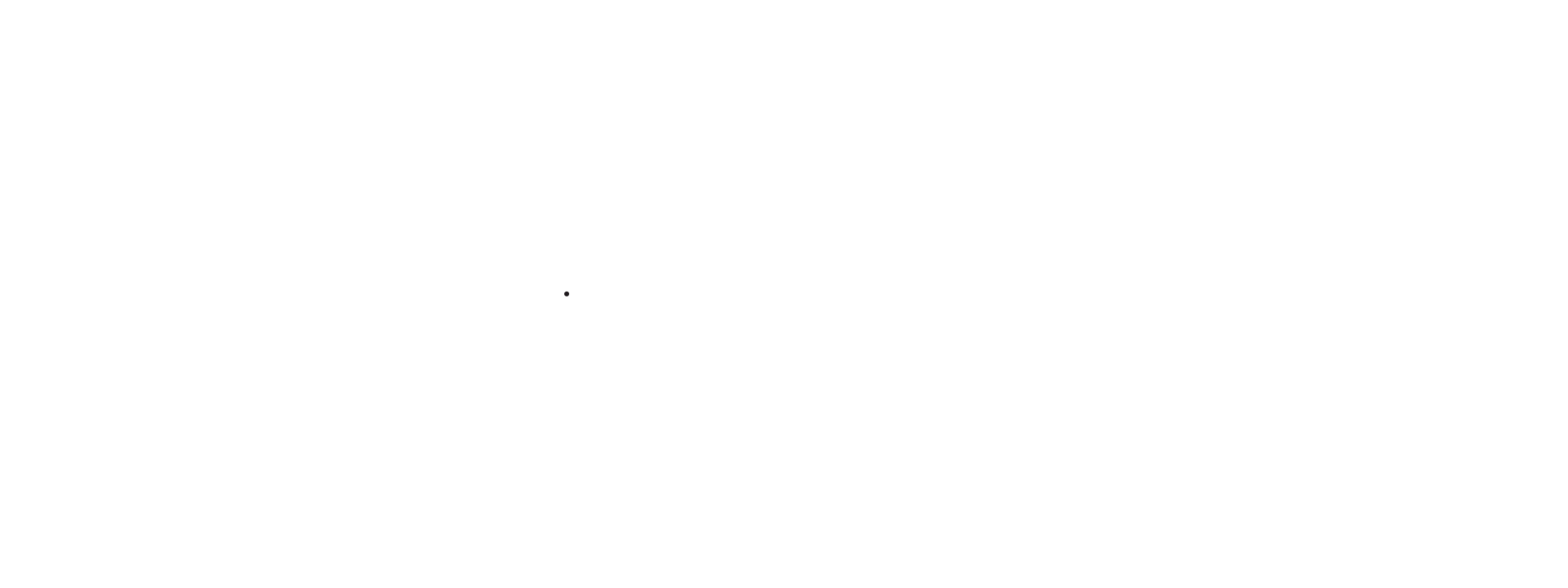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林:潘老师,提西南艺术研究群体,提到新具象,我们都会把你们四位联系在一起:张晓刚,毛旭辉和你放在一起比较,像张老师最近在外面的展览比较多,受关注面要大一点;叶帅现在涉及策展这一块,他可以在艺术圈和策展圈都比较活跃;相对来说,你是这几人当中最不活跃的一位,是什么样的原因呢?我听说之前你是最活跃的。
潘:很活跃?其实也没有,相对来说那时候更年轻一点,刚刚毕业比较愤青嘛,所以才比较积极,做事情比较果断一点,比较敢闯敢说,但这也是相对于现在来说,其实就我整个人来说,我觉得我变化不是很大。
林:我知道你经历很多波折,你说现在你大部分时间都在画画,但当时“新具象”之后,你南下深圳打工?
潘:那是80年代的事了。1985年在上海和南京,刚办完新具像展览。那个时候做展览跟现在的展览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完全想不到现在的展览是这个样子的,也想不到,我们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更想不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也没那个精力去想这些,当时比较苦闷,那个时候我们画画都是自给自足,不像现在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完善,什么材料都可以买到,当时画框画布都是要自己做的,可能你现在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当时真的连画布都没有,我们都是用那种纺织厂当时做为包装棉布来画画。其实整个画画过程更像生产劳动。而且那个时候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每个人都还有自己的工作都是用自己的工资来支持画画。
林:我听人说好像当时你们做展览的时候,你凑的钱是最多的。
潘:我忘了,大家好像都凑钱了。因为,那个时候办画展一切都要自已想办法用钱的地方很多,凑的钱许多都用在了把作品寄到上海,做包装和运费上了。今天想来也不算多贵也就几百块钱。可在当时看那可像天文数字。
林: 你当时是借了钱来参加这次展览,后来去了深圳打工来还钱?
潘:对的,当时我们都没钱,一个月工资才几十块,根本不够支付画展的费用,就只能借钱了。那个展览结束以后,我们几个人等于已经把自己的家底完全掏空了。但是,我又想不能就这样停止画画,还得画画还得做作品,但是怎么办呢?人还要是生存,生活还要继续还得找生活的出路。没办法只能去深圳试试了,因为有许多朋友已经去那边了,因为,当时深圳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是最开放的,最先开发的地方。
林:那你有没有挣到钱回来?
潘:没有,其实当时也不是完全为了挣钱去的,也是想去看一看,看看能不能有其他的出路,艺术上面,其他方面也好,想看看有没有改变现状的可能性,虽然钱不多,但是跟内地相比还是多的,毕竟,我们也只是去打工的。
林:那你去了多久?
潘:一年左右吧,在那一年里,我可以说没有完全脱离艺术,还是在做创作。
林:那一年还是在画画吗?
潘:没有,画倒是没怎么画,主要是在做一些陶类的作品,一些好玩的随笔和设计之类的东西。
林:那个时侯最重要的就是坚持理想,你成为了历史人物。我听说你从深圳回昆明的时候,钱被偷了?
潘:我在车站打电话的时候,包被偷了,除了自己身上的衣服,其它的放在包里的东西全被偷了,包括钱,证件之类的。那个时候打击是很大的,我在深圳工作一年,拍的各种创作的照片,反转片结果全被偷了,等于那一年完全变成空白了,真是一无所有两手空空的回到昆明,当时已近绝望,幸好有朋友借钱让我能返回昆明。
林:当时,谁还在昆明?
潘:当时昆明只有大毛(毛旭辉)在,张晓刚已经去四川美院了。
林:你86年回来的时候就去了中学教书是吗?
潘:是的,我从大学毕业以后来云南就去学校教美术,其实也一直断断续续的教书,因为教书很痛苦的,学生都是地矿局的子弟、学生很难教。
林:你回来的那个时期画了什么?
潘:从深圳回来以后继续画抽象系列的作品。
林:聊聊您当时的作品。
潘:最早的?我大学毕业刚从东北来到云南,我82年底来云南的时候画的都是抽象的作品,当时画的作品都还有点大,很小的房间很快就堆满了。画都是用包装布或是以前用做天花板的纤维板,而且是属于最粗糙那种材料制做容易变形。就是这样差材料当时也是无处寻、碰上学校拆房我才要了几块。另外还有帆布画材料,甚至床单我都用上了。
林:我听说你当时工作的地方还是毛老师母亲工作的单位。
潘:是的,这真是缘份、我跟大毛的母亲是在一个学校教书的,而且还住在一个院子里,虽然我去的时候大毛的母亲已经退休了。本来我在云南是一个人都不认识的,其他人都以为我在云南有朋友,不然怎么会一个人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到云南,其实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就是大学一毕业突然就来到了云南。当时,我住的地方就是一间小平房,大毛的母亲就住在离我住处不远楼房里,大毛又常常回家他那冲冲身影总会引起人的注意。我的房子没有窗户,又黑又潮,屋里比外面低,我白天也要点灯,为了让房间亮些和避免潮气,我每天都开着门画画。那时候大毛时常从我门前走过去,我那时候就觉得大毛可能是画画的,因为他那留着长头发穿着大大的毛衣背着民族黑包,有一天大毛突然来到我房间看我画的作品,我们一边看画一边谈起我们所喜欢的画家以及他们的艺术、发现我们是志同道和之人、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就这样我在异地他乡终于有了好朋友、那也是我人生重要的开始。
林:你当时为什么想来云南?
潘: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想画画,想创作想找到有感觉有梦想的地方就是想当艺术家,当时我也不是很了解云南就知道那里是我认知以外的另一个世界。一次一本白描的小册子,上面画的全是版纳那些地方的白描画。深深的吸引了我、那时就觉得云南是非同寻常的地方,然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比如高更,梵高,塞尚等等对艺术的执著和那种艺术的殉道精神让你的生命和人生有了新的意义和奋斗目标。我是跟随着梦想一路来到了云南。
林:那么你当时是不是觉得画家艺术家就应该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边远的村庄,一个部落才可以更好的创作?
潘:是的,因为艺术创作需要不同感受和体验。也是因为受高更和梵高的这种艺术家绘画的影响。
林:你当时毕业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来这边工作的工资刚好够糊口,也没想挣钱的事?
潘:是的,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想能够创作画画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那时大学毕业还可以申请去你想去的地方工作,当然大多都是边远之地。我那时候就特别积极,自愿申请表填写了云南,四川,就是不想留在东北,因为那里我太熟悉了,就只想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林:我看了你前期的作品好像是具象的比较多,为什么上大学的时候和毕业来了云南以后风格变了那么多?
潘:我后面也在反省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上学的时候写实的东西画得太多了,长时间受写实艺术的影响人的思想与观念会变得麻木失去了活力去创造力,后来在大学接受了西方现代主义艺术的影响,虽然那时候有些艺术作品还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就是觉得很有意思,很新鲜,很真实很有艺术创作性的想象力很想去尝试一下。我在学校的时候其实画得比较保守更倾向于西方古典主义、喜欢深沉严谨的艺术风格。到了大学后期才开始慢慢的尝试,画了很多带有梦幻和超现实的东西。
林:比如说,你来了云南以后,到一个中学教书,住在那么阴暗的房子,学生也不乖,情绪上有没有什么冲突,觉得不是想象中可以画画的地方?
潘:肯定和当时想象的不太一样,重要的是艺术,只要能画画。工作与住房等条件差点都不是太大的问题、有些是可能会得到解决和被克服的,学生的确不乖、教中学美术真的让人头痛、学什么好像都不重要了、每堂课能想办法维持课堂记律变得比讲课本身更重要、你的精力和辛苦完全用在了与美术无关的方面去了、这会让你很失落很和无奈、这方面会逐渐失去耐性。不过还好每年都有假期让你有很多时间去作画、这也是我最满足的地方虽然创作空间并不那么理想。
林:你当时的工资是完全够生活的,是吗?
潘:工资基本还是够用的、当时生活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大开销就是吃饭抽烟、买书和音乐。这主要还要看当月的经济状况而定,甚至有时还可以买几管颜料,有时朋友会送些画布和颜料给你。
林:您当时拿到画布的时候完全不用想会不会浪费这块布?
潘:不用想,因为那不应该有你考虑。你要考虑的是把想要表达的东西很好的呈现出来。
林:等于是对过去对学生时代的一种告别?
潘:我当时也觉得奇怪,我学生时代学的都是很严谨的画风,基础打的也不算差,怎么会一毕业就完全开始画抽象画了。这可能与大学四年的寒窗生活接受西方艺术教育及思想观念有必然因果关系,无论在哪方面你都积累了很多东西、可是又没有完全可能性去尝试和呈现。可是你的世界观你的行为方式己经不是原本的你了、从学校毕业出来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价值观的根本改变也导致了思想及观念的解放。学生时代一旦结束心灵的自由与涌动的思潮也随之象被打开的闸门一样一泻千里、心灵与环境的变化给精神带来了新的体验一切都处在变动之中也给现实与未来蒙上了梦幻和忧郁的色彩。所有发生的一切似乎无法在想以前那样寻规倒距的正常生活、一切都倒着来了、午饭变成了早餐、夜晚好像白天、白天从来就没有感觉只有到了夜深人静时创作的欲望才像泉水般的涌来,那时产量真高哇。
林:我觉得你那一时期画画都还是很快的。
潘:对,我都是半夜12点开始画,很快的就可以画完,有时一天可以画好几幅。一次偶然的机会发现了土林、然后土林系列创作又开始了。
林:那个时候你已经有了一些旋转的笔触了。苞米系列是什么时候开始画的?
潘:在87年左右,新具象之后。在做新具象的时候,我已经有了很多的作品积累了,包括土林和抽象的作品。
林:当时做新具像展览的时候,这一系列的作品去了多少幅?
潘:一个人有二十多张画嘛,这些作品都在。我跟大毛的作品都比较大,张晓刚的画要小些,那个时候我们都是高产。苞米系列是我在从深圳回来以后画的。刚回来的时候也在画,但更多的是在找感觉。
林:你当时画抽象作品的时候,国内画得还比较少吧?
潘:对,至少云南还很少,因为受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影响极大,尤其像毕加索,梵高,以及超现实主义、极少主义和抽象表现主义画派与主张,还有集中大量的阅读了刚介绍进来的西方名著、如近现代哲学,现代派文学、心理学等。那种抽象的感觉和意象还最能表达当时的情绪和状态。
林:当时学院老师教的都是苏联的那一套?
潘:对,当时加教我们的老师有中央美院、鲁迅美院和折江美院的,他们大多应该都是受前苏联现实主义和契斯恰克夫美术教育体系的影响发展起来的,所以教我们的也是他们所学的东西。
林:你最初学画画是怎么进入状态的?
潘: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记得那时每次新订好的算术本就在封面上画小鸟。
林:你当时学画画的时候不是对着石膏之类的静物画、而是一开始就画人?
潘:真是这样。中学一年级时市里文化馆要开办美术学习班、学校就推荐我去。美术班第一堂课就是学习怎样画人物、怎样勾线。后来分班我被分甲班、由从鲁美刚毕业不久耿老师教我们、从那时候起才开始正规的学习素描。也是从简单开始、从石膏几合形体再到头像胸像。
林:当时家里是没有活让你干?
潘:有,我父母白天都在上班,家里兄弟姊妹有五个人,加上父母全家七口人、我在兄弟中排行老二。劈柴生火做饭挑水喂猪打扫卫生、什么都做。
林:你当时除了在文化馆学习班上课以外就是自己在家里抽时间画画?
潘:对,就是一边做饭一边在旁边画画、当时主要是临摹小人书。(连环画)
林:我学画画的时候也是在文化馆、我老师当时告诉我画画想要画创作就先看看小人书(连环画)让我临摹练习构图、你当时也是这样的心理?
潘:不是的,我当时画连环画完全是自己喜欢,我的老师只教我们画素描、石膏像、水彩和风景画。我自己特别喜欢勾线人物画、比如当时著名的连环画《白毛女》、《山乡巨变》,我不但把整幅画面临摹下来还把文字也写下来、那时就梦想将来一定要当个连环画家。
林:大家对你的了解大多都是从你的苞米系列开始,表现性的绘画,很少见到你画写实风格的作品。前段时间,你参加《礼物》的那个展览,展出了一些速写,功力棒极了!像这种功力联系到你读大学的时候算起来应该有十多年了对吧?
潘:有了,从1978年上大学开始算、到现在差不多也有二十多年了。其实自从开始学画画一直没怎么间断过、至少画速写是没停过。因为简单方便什么时候什么场合都可以画,还有画速写会上瘾。
林:你当时跟那个老师学了多久?
潘:自从在学习班认识了教我们画画的耿老师以后、我就一直跟着耿老师学了。后来中学毕业下乡,在农村插队落户的那些年也没停止和老师联系。还经常把在农村画的速写给拿给老师看、一直到上大学的四年学习期间我和耿老师之间也一直保持联系、把学校画的画让老师看、看老师有什么意见和看法。工作以后也有通信往来。后来我去云南了、但是每次从云南回东北我们都要聚一聚。我在农村的那几年画很多当地的农民、都是铅笔画、我也喜欢他们。我下乡那个地方靠近内蒙是沙土地、偏避贫穷落后、是一个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一个壮劳力干一天活也就能挣几角钱、房子都是沙土盖的、当地人叫‘干打垒、风很大、干活回来全身上下耳朵眼鼻子嘴里都是沙子。所以当地人都是沙眼病。
林:当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发生?
潘:你指爱情?都没有,不仅我没那个福份其他人也没有发生什么故事。还有我们那个时代人是很传统的。农村的劳动很辛苦天不亮就要起床下地干活了、睡得也早天一黑就上坑睡觉了。有的时候粮食吃光了就只能吃土豆、有时把人吃的直拉肚子。那时我们烟抽得很利害、都是农民自己种的。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