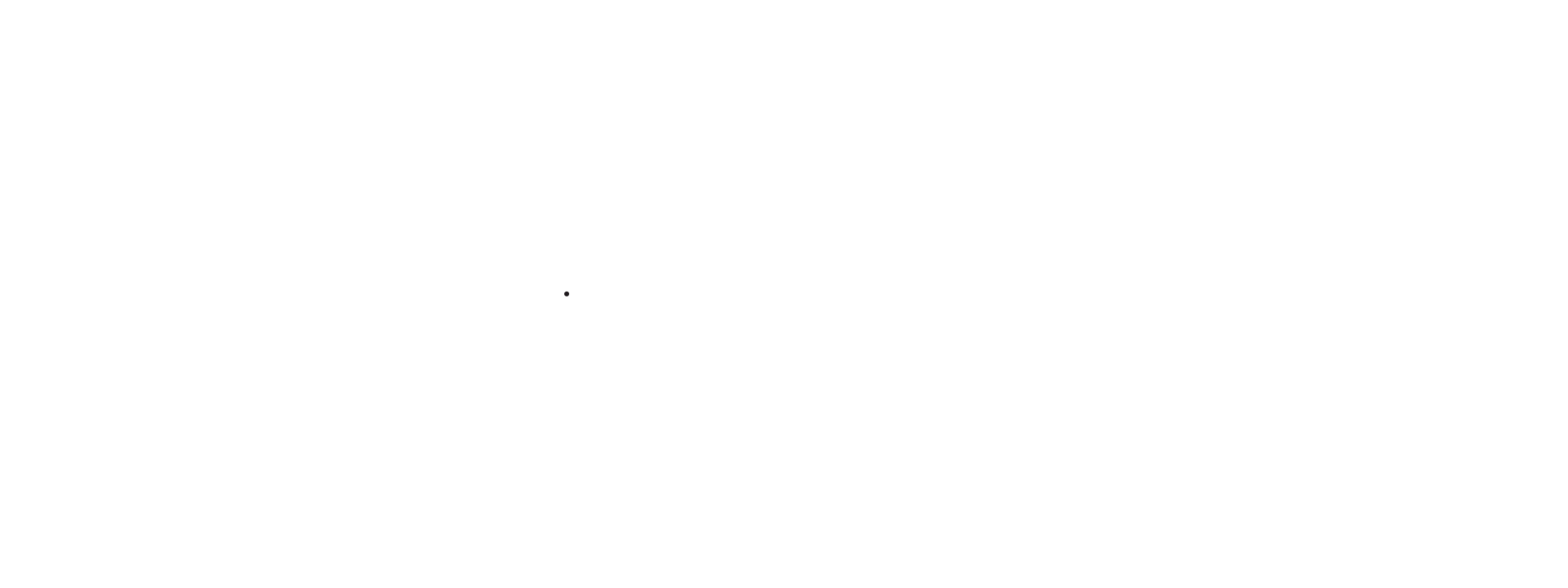
赞美它,就是批判它,反之亦然——薛松印象
就这样一个人,做出了非常有野心的作品系列。那种连续不断的规模具有扩张性,有点像当年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闯入了欧亚大陆,在那片广阔的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插满了薛松的旗帜。但他的作品并不只是同一个图式,虽然它们都像一面旗帜一般容易辨认。薛松是注意细节的,为此他买了大量的书籍。我与薛松有一个共同的爱好——买书。我买书是为了读,薛松买书是用来烧。薛松的细心表现在他对不同题材的处理时,对所用图片的精心选择常常达到了接近考据学的刻意程度。除了前景的主要形象,薛松在处理作品背景方面,所花费的时间和材料密度往往大大超过了前者——无论是作为衬托还是作为对比,有时候是从属于主体的,有时候却完全是陌生化的,彼此不相干的,以此产生时空与意义的错位,以及隐喻的多义性和模糊型。看来薛松的思考很缜密,我得承认我低估了他理性的一面。
因为他做这个作品需要烧书,烧书之前需要选择书,于是他还必须读书,哪怕是浏览书。这样一来,薛松就涉猎了大量的历史知识,他以前是不在乎知识的,现在他不同了。薛松的方法是百科全书式的,他几乎可以把全部信息都拿进他的作品,一个图像,一个符号,把世界全囊括了。在这个回顾展上,我特别注意到薛松的几件早期作品,当年都看到过,我还有印象,现在好像都修补过了,也许是从收藏家那里借来的吧……当时他的这些作品明显透露出一个丧失了方向的年轻人的焦虑和焦灼,一种无方向性,不知道应该干嘛,那种内心的烦燥、紧张感、力度,统统都在里面。现在不同了,他开始走出个人,进入时间,越来越有志于引入多个知识领域,薛松好像期望成为教授艺术家,确实,在他的作品内部可以建一个历史博物馆,或一个图书馆,也许是巧合,薛松的作品很适合在图书馆展出,而上海美术馆的前身就是上海图书馆。我感谢薛松,当年我在他的画室里多次度过了美妙的时光;现在,二十年过去了,我为他版图的扩张感到很高兴,虽然他现在似乎已经无所不能,轻易将一切收入囊中,使他的作品色彩斑斓,而不再像过去那样沉重和充斥了嚎叫。我想起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时代,我们将它留在了身后,同时留下了对那个时代的记录。但今天的时代全变了,我们依然常常觉得迷惘、混乱和不知所措,也许薛松的态度正隐藏在他色彩斑斓的新作品背后——我们对历史和现实依然无能为力,我们赞美它,也许就意味着批判它,反之亦然。
——吴亮 上海作家协会驻会专业作家,著名文学批评家
Copyright © 2017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阿特多多 版权所有